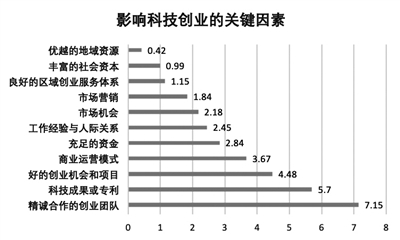
影响科技创业的关键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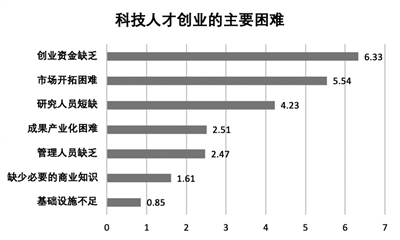
科技人才创业的主要困难
一身黑衣,并不引人注意。总是处在严肃的思考状态。
吴乐斌突然意识到,坐到自己邻座的是物理学家潘建伟院士。
作为时任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控股)董事长,吴乐斌在很多会议上见过潘建伟。但个人交流还是第一次,还是在一趟从北京到合肥的飞机上。
那是2015年春天,离量子通信的大火还很远。当时潘建伟等人联合创办的国盾量子刚成立五六年,几乎是一个没有销售额、没有利润、没有固定资产的“三无产品”。少有人相信,他们做的事可能带来一个崭新的通信时代。
飞机一路飞,潘建伟一路讲,吴乐斌意犹未尽。
“当面讲起来有逻辑、有趣味,讲完都懂了,站起来转个身就不懂了。”吴乐斌笑言量子通信高深莫测,“我说赶紧再来,咱们继续谈。”两人很快约了第二次见面的时间,仅仅两周后,潘建伟又来到北京。
一来一回,靴子落地,吴乐斌推动国科控股投资国盾量子。1.52亿,第一笔国有资本注入量子通信。
“压力很大。”吴乐斌坦言,把这样一笔称得上巨额的天使轮投资拿出来,遭遇很大的阻力,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没有人知道钱会不会打水漂,“还是国有资产”。
后来的故事广为人知。
去年7月,国盾量子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涨幅超1000%,破科创板纪录,收盘估值近300亿。
近段时间,潘建伟领衔的科研团队成功构建世界上首个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标志着我国构建出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雏形。
一边是“脸难看、钱难拿、弯不下腰”的科学家
在吴乐斌看来,这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合作。
更多的时候,他要为科学家的“个色”捏把汗,“如果科学家不按常识做事、难以合作,就很难获得支持。项目就会被扼杀在萌芽里。”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了很多人。”吴乐斌笑说,板凳甘坐十年冷,科学家在长期苦心孤诣的研究历程中,必须要对自己的研究非常笃定,否则很难坚持。但这也造就了科学家比较坚持己见的态度,以及放大成果意义的倾向。“成果本身很好,但科学家有鲜明的个性或者说很‘个色’,增加了合作的困难。”
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院士有句话流传甚广: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励科学家创业。在他看来,术业有专攻,鼓励擅长科学研究的人办公司、当总裁,是把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此话虽有争议,但也得到很多人的共鸣。
“科研人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科学家,做公司的短板很明显。”一位学术成果丰硕、在芯片行业创业近10年的科学家坦陈,“我自己的短板就很明显。比如我经常被老大数落,说我不愿意拜访客户。可是拜访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你的学生辈,还对你吆五喝六。他们和科研人员的气质完全不一样。身边很多创业的老师说起来都头疼这点,就是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脸面和身段。”
他话说得实在,有成果在手、有底气创业的科研人员本来就在科研院所里备受尊重,本身也多是国家级人才,一下到了市场上俯下身去,心理落差明显,“一般受不了”。
在吴乐斌口中,这道坎儿更直接——“找钱”。
上个世纪80年代,有美国学者发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是制约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即科学研究与商业化产品开发之间严重脱节。1998年,时任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副委员长Ehlers将其命名为“死亡之谷”。
“越谷”不易。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开发服务处处长牛萍遇到过很多踌躇满志的科学家,试水创业后回归学界,原因不外乎——“脸难看、钱难拿”。
科研院所的院墙内外有着完全不同的气候,科研人员往往要花很大力气、栽很多跟头才能适应。
一边是追快钱,急回报,“耐不下心”的投资者
一边是“看不上钱”的科学家,另一边则是“看不上科学家”的投资者。
在吴乐斌看来,这种“看不上”并非看轻,更多是缺少判断力和耐心,“科技成果的转化,本身也是‘高科技’。”
“有一次参加成果发布会,有人告诉我,采一滴血就能告诉我全部的身体状况。”吴乐斌说,“我很好奇,问他一滴血看的是什么,对方告诉我看的是血液形态、细胞形态,看显微镜下血液的有形物质。”
本来兴趣盎然的吴乐斌开始起疑,“这不符合基本科学原理,目前没有一个医学原理说明细胞形态能够囊括身体的健康信息。”他强调,无论科研成果多么酷炫,基本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科学原理,既有创新性,又要有继承性。
有趣的是,如果没有把好这道科学关,故事的走向可能大相径庭。有个现成的例子——“坏血”。
Theranos几乎是本世纪最戏剧化的科技创业公司。2014年,年仅19岁的伊丽莎白·霍姆斯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创立Therano血液检测公司,宣称发明了新技术、新设备,只需刺破手指采几滴血,就可以完成在专业医疗实验室内进行的多达240项身体检查。
这个革命性的验血设备让她“斩获”“女版乔布斯”的大名,以及近百亿美金的估值。
但伴随着调查记者约翰·卡雷罗的不懈“扒皮”,这个创富神话被证实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从来没有革命性设备,只有设备和数据的层层造假。一个持续十几年的“坏血”骗局震动全球。
判断成果的科学价值之外,更宝贵的是静待种子发芽成长的耐心。
“科技投资需要长线。市场上理解和尊重科技、对成果有耐心的投资者少之又少,大部分追热钱追快钱。”吴乐斌直言,他接触的有些投资者明显“把科研院所当成提款机”,“曾经有投资者简单不过地说非常看好某项成果,要给钱,但恨不得当年就要回报,最多两三年。”
面对早期成果,市场上投资者大多兴趣不大。“科学家要和投资者走在一起,后者不能对前者太急功近利。”吴乐斌说,比如寒武纪,如今的“AI芯片第一股”开盘后市值很快突破千亿元,无数人削尖脑袋想往里挤,但在他的记忆里,早些年几千万估值都鲜有人问津。
十几年研究所副所长加十几年投资者的经历,吴乐斌经手的项目形形色色。曾经有科学家发现从动物器官中提取的成长因子成分,可以治愈不容易愈合的创口,主动找到他,吴乐斌跟他详谈,设计了成果如何实现转化的路径,结果第二天,科学家告诉他“昨天晚上,差一点就死了”。
吴乐斌吓一跳。细问才知道,原来科学家听完心情很激动,一晚上没睡着,做医生的太太直接说,“算了吧,这么往前走我对你的健康很担忧,会影响这条命”。
“他是很好的科学家,有很好的科学发现,他对创新非常敏锐,导致他性格中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对美好前景既欣喜又担忧。”吴乐斌说,好的成果转化,需要科研人员、企业经营人员、投资者三方的和谐步调,缺一不可。
怎样才能让人和钱走到一起
吴乐斌常被看作“离科学家最近的人”。作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的掌门人、中科院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工作就是把钱投向有转化潜力的中国科学院成果。
在他看来,成果必须回应市场的真实需求,“起码要有商业计划书”。但能做到这一点的项目寥寥无几。
商业计划书可以回答成果转化的基本问题——你的技术解决了什么市场需求。
这能规避科学家的“自我欣赏”。他回忆,曾经有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同事,研发了一款致力于解决心脏衰竭问题的产品,“半衰期特别短,意味着针打进去还没拔出来,半衰期就没了。”
这不是个例。科学家“自以为是”的产品是成果转化的常见问题。“一项成果最好做到新、精、特、廉。”吴乐斌说,“廉”是说产品比市场成品的价格至少低百分之二十。
另外,成果要有可量化的指标,结果可重复。“有位科学家发现用一个频谱照射种子,种子发芽成长结果特别好,比如照了南瓜,南瓜就长得又快又大。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频谱的光照射种子时,种子的湿度、光照的时长、环境的温湿度。能不能告诉我这些指标和结果之间的线性关系,告诉我CV值(批间差)。没有这些,成果是不可信的。”
一串问号给热情高涨的科学家浇了冷水。吴乐斌说,从发现到发明再到样品、到产品,过程漫长。半路“转不动”的大有人在。
满足了这些,成果还要遵循市场准入。药品要有新药证书,医疗器械也有器械证书,只有遵从行业的游戏规则,才能进入市场。
牛萍坦言,技术越先进,和市场接受的时间差可能越大,“我们承载创新的丰厚土壤还不丰厚,技术需要主动找市场”。
从迈出成果转化第一步起,做商业计划书要钱,产品化要钱,这些需求没有对应的科研经费支持,也很难得到资本支持。在这段“爹不疼娘不爱”的早期市场化阶段,吴乐斌强调,正是科技资本发挥价值的时候。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表示,资本的逐利性与科研长期性存在矛盾。科技信用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它源于人们对科学知识的信赖所产生的社会共识。基于科技信用,科技资本对科研进行投资并预期实现增值。
“科技资本要在看不到实物的时候相信他,在产品不完美甚至没有产品的时候把钱给他。”吴乐斌说,要帮助科技初创企业走过“死亡之谷”,就要把三种人(科技人员、企业经营人员、投资者)以及四笔钱(政府科研经费、企业资本、保险、金融机构贷款)聚在一起。通过政府基金的引导作用,渡过市场“认钱不认人”的难关。
他尤其强调了科技保险的价值,“科研工作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资本身充满着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需要保险来对冲”。
据他介绍,科技保险覆盖了科技创新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使得科技投资不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今天的科技行业非常需要科技保险,目前很多科技保险并没有真正发挥科技保险的作用。因此,科技行业亟须中国自己的真正科技保险。”吴乐斌说。
